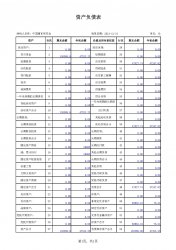以书为媒
汪恩甲离开后,东兴顺旅馆老板停止给萧红供应饮食,并把她赶到楼顶散发着霉味的杂物房,甚至准备在她确实无力偿还债务时,把她卖去妓院。
孤独无助的萧红只好写信给《国际协报》求助,诉述自己的遭遇,希望报界主持正义,帮她脱离困境。
《国际协报》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约上舒群、孟希等文学青年,一起到旅馆探望萧红,并想办法营救她。
萧军多次受裴馨园之托,到旅馆送书刊给萧红解闷,与萧红日久生情,互相爱慕。
此时哈尔滨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,东兴顺旅馆被淹,萧红被救了出来。
“小小红军”
萧军,原名刘鸿霖,辽宁锦州人,比萧红年长4岁。
两人的笔名“萧红”、“萧军”,合在一起便是“小小红军”。
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后,到裴馨园家暂住。
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,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。
出院后,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,开始共同生活。
因没有固定收入,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,生活非常困苦,但他们感情融洽。
1932年11月,萧红、萧军搬到哈尔滨道里商市街25号(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),有了自己的家。
《弃儿》
在萧军的影响下,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
1933年4月,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弃儿》。
据说,这篇小说与她将自己孩子送人的经历有关。
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《我的婶婶萧红》一书中,委婉地批评了萧红对她与汪恩甲的女儿的绝情:“六天,萧红没有看孩子一眼!六天,没有喂孩子一口奶,那奶水涨得湿透了衣衫。孩子咳嗽的声音,从隔壁传过来,她把心紧成了一块铁。贫困,把做母亲的女人挤压成如此冷酷!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,母爱一旦泄出,将一发不可收拾。一眼都没瞧一下的孩子,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。以后的事实表明,这孩子成了她抹不去的伤痛!”当萧红在香港病危交代后事时,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。
发表小说《弃儿》后,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《王阿嫂的死》、《看风筝》、《腿上的绷带》、《太太与西瓜》、《小黑狗》、《中秋节》等小说和散文,从此踏上文学征程。
《夜哨》《跋涉》
在道里水道街(今道里兆麟街)有一处平房,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,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“牵牛坊”。
萧红、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,常来的还有罗峰、白朗、金剑啸、舒群等人。
通过与他们接触,萧红开阔了眼界,增加了文学知识,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。
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,与萧军、白朗、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“星星剧团”中担任演员,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。
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,剧团于公演前解散。
1933年8月,长春《大同报》文艺周刊《夜哨》创刊,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,在夜哨上发表了《两个青蛙》、《哑老人》、《夜风》、《清晨的马路上》、《八月天》等许多作品。
10月,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《跋涉》,由萧红署名悄吟、萧军署名三郎,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,自费在哈尔滨出版。
《跋涉》的出版,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,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,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因《跋涉》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,引起特务机关怀疑。
1934年,萧红、萧军摄于离开哈尔滨前夕。
从哈尔滨到上海
为躲避迫害,萧红、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,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,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。
在青岛,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。
萧军在《青岛晨报》任主编,萧红集中精力,勤奋写作,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。
此间,他们与身在上海的鲁迅取得联系,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,当年11月来到上海。
在上海,萧红、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,向鲁迅请教。
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,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,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,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
裂痕
正当萧红、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,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,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。
其实,在和萧红一起的日子里,萧军先后和不同的姑娘发生过情感纠葛。
根据林贤治《漂泊者萧红》中的说法,在哈尔滨不到两年的同居生活中,至少有三名少女,同萧军发生过暧昧的情感关系。
萧红在散文集《商市街》里提到,她们是:敏子、汪林、程女士。
程女士原名陈丽娟,笔名陈涓,宁波人,萧红对她特别敏感,在诗中写过专章:“一个南方的姑娘”。
没想到,程女士又在上海出现了。
这时的萧红,“烦闷、失望,哀愁笼罩着整个生命”。
暂别
为了求得解脱、缓解矛盾,情绪低落的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。
1936年7月16日,萧红离开上海,只身东渡日本,并且经常给萧军写信以诉衷肠。
当年10月19日,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。
噩耗传到日本,萧红悲痛不已。
萧红给萧军的那封“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”的信,写于当年11月19日。
信中所说的“黄金时代”,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、激扬文字的大时代,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、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,外人无从得知。
然而,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,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、身体的伤病、舆论的微词,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,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。
1937年1月,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。
萧红和萧军的关系也有所好转,还参加了萧军编的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的资料收集工作。
分手
9月28日,萧红、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。
不久,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。
1938年1月,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,萧红、萧军、端木蕻良等人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。
2月,临汾形势紧张,“民大”要撤到乡宁,萧红、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,萧军先是留下,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。
在西安,萧红、萧军正式分手,此时萧红已经怀孕。
“我们过得很快活、很有诗意、很潇洒”
二萧相恋六年,最终分手。
萧红这样描述和萧军的感情:“在人生的路上,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,也踏着他的脚迹;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。”
二萧分开多年后,萧红偶然在胡风家里看到萧军再婚的结婚照,她惘然怔在那里泪流不止。
在弥留之际,萧红仍对萧军有所期盼。她说:“如果三郎(指萧军)在重庆,我给他拍电报,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!”
散文家戴永夏撰文,讲述萧军晚年时和他谈萧红的情景。
说到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时,萧军说:“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,只有十年光景,总共创作了110万字。”“她虽然很有才华,但由于贫病交加,她的身体一直很弱。她戏称我为‘壮牛’,称自己是‘病驴’……”
二萧的通信中,彼此常用“小海豹”、“小狗熊”等外号相称。
萧军回忆道:“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,政治、社会环境是恶劣的,但我们从来不悲观、不愁苦、不唉声叹气、不怨天尤人、不垂头丧气……我们常常用玩笑的、蔑视的、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,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,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。比如,我称萧红‘小麻雀’,是形容她腿肚细、跑不快,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;称她‘小海豹’,是说她一害困、一打哈欠,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,俨然一只小海豹;称她‘小鹅’,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,两只手就左右张开,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。而她称我‘小狗熊’,则是因我笨而壮健,像狗熊似的……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,因此虽然很穷,但过得很快活、很有诗意、很潇洒、很自然……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!”
谈起和萧红的关系,萧军说:“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,可以说患难与共、相濡以沫,谁也离不开谁。可是,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。尽管彼此爱得很深,但我的粗犷、爽直、强梁的个性,常使她那纤细、脆弱、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。我们俩在一起,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,太靠近了,就要彼此刺得发痛;远了又感到孤单。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,往往容易引起裂痕,引起误会和猜疑,结果带来痛苦……”
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则认为,“虽然二萧之间有很大的差异,但都不是他们分手的必然因素,萧军对婚姻和爱情不忠,才是本质。”
光阴荏苒,当爱已成往事。
正如萧军在悼萧红诗中写道:
“生离死别已吞声,缘结缘分两自明!早有《白头吟》约在,陇头流水各西东。”